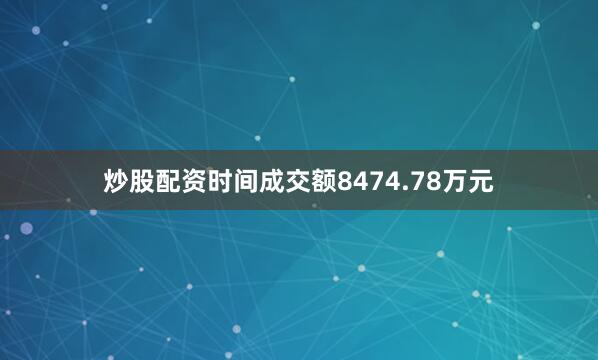地主少爷当了军区副参谋长,评衔时毛主席看中将名单:怎么没见他?
【序章】
1955年的授衔名单里找不到他的名字,毛主席拿起名单,眉头紧锁,问道:“周骏鸣怎么没在名单上?”在场没有人敢回答。
出身于地主家庭,却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
在1902年的河南,周家大院是一个围墙高耸、院落深深的大家庭,居住着上百号人。
老周家祖上是地主,家里几代人不是种地就是做买卖,日子过得挺风光,门面也挺阔气。周骏鸣是家里的老三,从小跟着先生念书写字。可到了十七岁那年,他突然扔下笔,说要参军,这可把家里人给惊着了。没人明白他为啥突然这么决定,问他,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文人没用。”后来,他就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。

他刚当兵没多久,亲眼看到一个上校军官偷偷拿走了军饷,结果前线的士兵因为没有吃的,一个个饿死了,尸体堆在河边,没人埋。他站在河堤边,盯着看了一夜。
西北军有个规矩,对老百姓要像对子女一样爱护。但是,他们在战斗中却毫不手软。每到一个地方,他们要搜刮粮食,打土匪,还要杀掉地方上的反抗者。打完仗后,他们把战利品分给大家。军官多,士兵少,他见识到了“军阀的作风”。
1931年,宁都发生了起义,他带着自己手下的一个连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那时,他已经是一名连长,手下有兵,对武器也很熟悉。起义成功后,红军接纳了他们,他加入了红五军团,并被任命为115团的团长。这一年,他29岁。
红五军团在赣南地区安营扎寨,毛主席时常前来巡视。有一次,毛主席在一个山间的小屋里召集军官们开会,他说道:“我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,如果不与百姓紧密相连,红军就难以持久。”
那个晚上,周骏鸣把这句话记了下来,放在腰间的口袋里,一直带在身边,过了十几年也没舍得丢弃。

1932年,红五军团的一些军官被遣散。原因是起义部队的成分太复杂,难以进行整编,有些人贪污,有些人逃跑。军委决定采取措施进行清理。
周骏鸣因为家庭背景复杂被列入了遣散名单,但他没有闹腾,只是找毛主席谈了一次话。
毛主席说:“你走,革命别停,拉队伍,建根据地。”然后他就回去了,去了河南。
那时候,河南的地方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军队。周骏鸣被选为河南军委书记,主要任务是推动农民运动。
他召集了一批老部下,开始在豫东地区组织暴动。他熟悉地形,也懂得如何利用人脉,很快控制了几个县乡。
1934年春天,党内发生了变故,一个联络员背叛了组织,导致周骏鸣被抓住了。他被戴上手铐送到了开封的监狱里。敌人审问他三天,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敌人说他顽固,他说愿意“合作”,并要求见特务的头目。

在会面时,他揭穿了伪省委设下的陷阱,破坏了敌方的计划,随后却被假释了。
他刚出狱,就没回县里,直接躲进了铁幕山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,不想牵连到别人。一个月的时间里,他只带着6个人,配了3条枪,开始做起了游击战。

游击战的精彩故事和军队生涯的辉煌时刻
铁幕山虽小,但地形曲折多变,南边是茂密的树林,北边则是陡峭的悬崖。周骏鸣领着队伍进了山,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搭起了营地。
他们白天休息,晚上则下山偷武器、抢粮食,还放火烧毁敌人的据点。由于敌人反应迟缓,没意识到山里藏着红军队伍。两个月后,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三十多个,武器也换成了汉阳造。

1936年,山里已经有七八支地方武装,他将它们合并,成立了豫南红军团,一共有1300人,其中接近400人有枪。每天都要进行操练,纪律非常严格。
遇到抢劫百姓的,枪毙一个,解散一批。“这不是土匪,是红军。”他只说这句。
毛主席在延安得知豫南有队伍后,派人进行了调查。1937年,周骏鸣被邀请到延安汇报工作。
毛主席见了他,谈话时间很短,问的全都是具体问题,比如“粮食是怎么来的?”“干部们在哪里接受培训?”“地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?”他都一一作了回答。
毛主席最后说:“国民党不和我们谈,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强,弱了就要打,一直打到他们不得不和我们谈。”
这一年,新四军成立了。他的部队变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,由陈毅和张云逸领导,他当上了副团长,负责战斗指挥。

1939年,半塔集被日伪军包围,敌军有三个团,想消灭新四军的主力。周骏鸣主动请缨,带领八团守在半塔的北面,吸引敌军主力进攻。
他布置了地雷阵和三层火力点,坚守了三昼夜,最终成功反包围,歼灭了上千敌人,俘虏了二百人。这场战斗为新四军树立了威望,被称为“半塔保卫战”。
战争结束后,陈毅在一次总结会上提到:“周副团长守的是我们南线的命根子。”说完这话后,周副团长没有立即回答,而是在那晚独自巡视战场,一一检查战士们的遗体,核实身份,并记下他们的名字。
抗战后期,八团扩大规模,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后勤处处长,参与豫皖苏战区的后勤工作。
1949年,他被调到华东军区担任副参谋长,协助粟裕负责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。他提出将徐州南线的主要补给路线改为通过泗洪和宿迁一线,避开铁路封锁,确保了三百多万斤粮草的供应,没有一天中断。

搜索图片
在长江战役之前,他负责修复了苏皖地区的堤坝,并设置了七个渡口,确保主力部队能够顺利过江。任务完成后,他向参谋部递交了辞职信,理由简短而明确:“战斗已胜,是时候让位了。”

关于授衔的争论:历史遗留问题与离开军队的关系
1955年,确定了授衔的名单。总参谋部在审阅报告时,副总长指着一页问道:“这个人怎么没写上,周骏鸣呢?”
没有人敢接话,名单上确实没有。

评定军衔时主要看三点: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、战斗中的表现和现在的职位。周骏鸣在这三个方面都符合条件。他是红军时期的团长,后来又担任过新四军的副团长,还有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。根据这些标准,他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翻阅档案,发现一页记录写着“1935年假投降事件”,被归类为“历史复杂问题”,还特意用红线标注,备注说明“保留意见”。
1954年10月,他离开了军队,改任水利部副部长,从军事序列转到了行政序列,因此自动不再参与评定军衔的范围。这并非组织的决定,而是他自己主动写报告申请的。
这份报告只有一页纸,字迹非常清晰,句子也很简单。
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可能会影响对我的评价,所以我申请离开现在的军队系统。
副部长的任命已经确定,级别是行政九级,这件事没有引起公开的讨论。在军队内部,大家都明白他是一位有着“红军背景”的老将,不过关于他的具体功绩,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。

有人说他害怕问题暴露,也有人说他知道自己授衔无望,不想再争了。老战友私下问他,他只说了一句:“不影响别人就好。”
毛主席在查看授衔名单时,问道:“周骏鸣怎么没有?”秘书回答说:“他已经调到水利部工作了。”毛主席继续翻看名单,手指停在一处,问了一句:“有历史问题?”之后没有再多说。
这不是表达立场,而是一种遗憾。
按照资历,周骏鸣的军龄和职务都比不少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人要高。一些老部下自己只是少将,看到名单时愣住了,问道:“老周呢?”

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,确保文章适合所有读者,不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或疏远。直接输出结果,不包括解释或注释的其他内容。
过去的半塔保卫战如今在新四军的历史展览馆中还能看到,但他并没有参加那次的纪念活动,也从未在任何将领的回忆录里被提及。
他没说什么,调到水利部后,主动搬出了干部宿舍,住进了工程院的老平房。下班后从不去军委招待所,总是穿着灰布中山装,在干部食堂吃饭,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来。

过往的回声与晚年的经历
周骏鸣到水利部工作后,主要负责淮河的治理计划。
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,他在文件上批注:“缺工缺料,可调军队施工。”没人理,他亲自跑了八个县查看堤坝走线。

有一次,在淮滨县的施工点,他和工程兵一起熬夜检查堤坝。突然下起了大雨,他脱下鞋,趟进水里,脚下一滑,摔伤了腰。他在医院住了三天,回到单位也没请病假。“我检查过了,南线三号口需要抢修。”
后来这个想法被大家接受了,给以后防洪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1975年,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,有三处堤坝决口。后来,相关部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。当时担任副部长的周骏鸣,虽然已经退休,但还是被点名批评,说他对工程决策负有责任。虽然没有受到处罚,但名义上他还是被认定为有责任的。
他没解释,从那年起,彻底离开了工作圈。
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小屋里,这位老人过着简朴的生活。这间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,窗台上种着几株辣椒,屋内只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。偶尔有老战友来探望,有人建议他参加将军访谈,但他都婉拒了,说不合适。
1990年代,有人提议为他写传记,他婉拒了。他说:“当时大家都讲究团结,我做的事情不算榜样。”

他经常在家里查找资料,用钢笔在信纸上记录回忆,没人清楚这些信是写给谁的。每写完一封信,他就把信纸折成三折,然后放进一个旧文件袋里。
2003年,他病得很重,住进了医院。最后一次说话,他对护工说:“把资料整理好,别乱动。”
11月9日凌晨,一位老人离开了我们。病历上写着“多脏器功能衰竭”,医院里登记他是“普通离休干部”。
到了下一年,一些研究党史的人在整理河南红军的历史资料时,重新找到了关于铁幕山游击队的线索。几位老战士回忆说:“我们是跟着周骏鸣出来的。”研究所后来联系了水利部,才最终确认了这些信息。
2006年,一本关于党的历史的杂志发表了《铁幕山起义考证》一文,首次提到了周骏鸣在反围剿战斗失败后,建立了游击根据地,为新四军的组建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
2010年,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专门为他设立了人物条目,条目的结尾这样写道:
作为地方上有名人家的孩子,他却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。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,他本可以功成名就,但他却选择默默无闻,隐姓埋名。历史的厚重,并不只体现在那些有名有姓的人身上。
富明证券-114配资查询-免费股票配资开户-配资平台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